东莞市浩深热流道:天香第三卷 设幔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偶看新闻 时间:2024/05/02 10:06:04
【零点书库】 天香第三卷 设幔

现当代作家
小故事大智
岑凯伦言情…
大功大过隋…
世界作家作
第二次世界
读者2011第
人生四大秘
寄秋言情小…

陈明娣言情…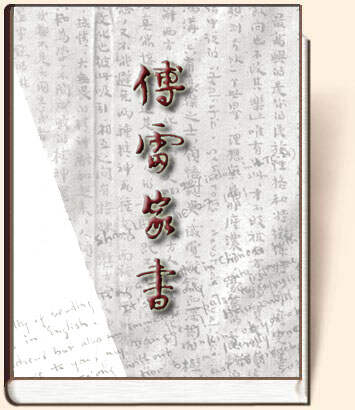
《傅雷家书…
《青春的叛…
姚雪垠长篇…
霍桑探案小…
南湘野叟武…
《山海经》
席绢言情小…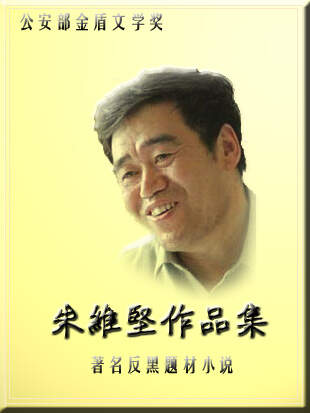
朱维坚作品












天香 第三卷 设幔
29九间楼
万历二十八年,上海的大事情都与徐光启有关。一是徐家在原先的宅基破土动工,造新宅子。地处方浜以南,肇嘉浜以北,日涉园西,背依一条小河汉,名乔家浜,门开在正南,俞家弄内。新宅子总共三进,并排九间,上下两层,人称“九间楼”。宅子的样式没什么新奇,也无奢华,在富户云集,风气绮丽的上海,堪称质朴。但就是这质朴,却因占地广大,建制充实,而有一种阔朗,还有一种端肃。要说造房子,本不算什么大事情,但联系上另一桩,也就是第二件大事情,便未可小视了。也是这一年,徐光启在南京,又结识一个意国人,利玛窦。和仰凰一样,也是洋和尚,却是个大和尚,要去京师见皇上。皇上不喜欢洋教,可是喜欢洋玩意儿,利玛窦带了无数稀奇古怪的器物,晋见的路已经膛平。这时,正走到南京,和徐光启碰上了。这徐光启,正途颇不得意,二十一岁中秀才,之后连连落第,丁酉年,好不容易中乡试,而且第一名,隔年的会试却又失利!年华就在这屡试屡败中过去,和许多读书人一样,也许就在幕府中度过一生。然而,又有迹象,暗示事情并未到此结束。好比徐光启踯躅科场多年,不期然里一突进,谁能断定,再下一轮踯躅之后又会发生什么?在外交游,竟先后与两个意国人邂逅,千山万水的,又非我族类,其中藏有怎么样的机缘?如今,九间楼起来了,坐地居中,登楼远望,东边一条黄浦江,奔腾向海。那意国人,不就是从海上来,应了变通亨达。因此,两件事一贯穿,便成了大征候。
这是祥兆,凶兆也有,不算大,小小的一桩。就是城南有一农家,大牛生小牛,生一怪胎,两头六足。有一时人心惶然,谣言四起,转眼翻过年头,人春便是淫雨不止,淹了麦田,都以为应了那兆头,不会再有其他灾变。也果然平定下来,风调雨顺三载,就到了万历三十二年。也是方一入春,黄浦江上忽起两股龙卷风,黑水腾起数十丈,在空中交汇,纠缠格斗,沿江大树连根拔起,茅舍尽毁。人们正议论,这才真是应了三年前两首六足牛犊的象,不料,倏忽间天降喜讯,松江府两士子中试,一是上海徐光启,中进士,入翰林院;二是华亭乔一琦,中武举,任京营兵把总。于是,坊间又改口,再不提那两首六足犊,只说,江上二龙相会,实是大气候,出将入相,将相和。
九间楼向北,隔乔家浜,过艾家弄几条横街,三牌楼南端新路巷内,一座小宅院,亦有着一桩喜事,张家二公子娶亲。张陛这年二十一岁,媳妇十九,数年前就下了媒聘。按说是早二年就当迎娶,不防出了些事故。三年前,媳妇的祖母,也就是申家老夫人去世。张家北地人的籍贯上有规矩,嫁娶或不出丧事的当年,或就必是满三年之后。申家一报丧,张家就紧锣密鼓筹备起来,可申家却推辞了,说姑娘年幼,家中一向惯养,不太懂事,再调教两年出阁更好。这是面上的原由,内里则是银两紧促,一时办不出像样的嫁妆。
那年,申家老太爷四下里采树造寿材,一回三折,到底觅来好木头,做了一套棺椁。木纹理细腻如凝脂膏油,紫光浮动,又有一股暗香。无论木材商还是大木匠,都认不出是什么木。申明世不由想起当年造天香园的章师傅,兴许能说出个大概,掐指算来也是七八十的年纪了,都不知道在还是不在。如今,最明跟的人只能说出产地,必是北方干冷的寒带,那里凡物种都不容易存活,非是天择不能落地生根。因生长极慢,数十年,甚而上百年一轮,质地紧密,犹如铜铸。那香自然是树脂的气味,也是因紧实原故,初不散发,年深月久,芬芳才缓缓释出,如同雾起。如今有此异香,必在千年以上。坊间都传闻,申家为寻木已花费大笔的银子,等觅到木头,就再拿不出了。要用田地抵,木主人不要,指明要天香园绣,不是一般的天香园绣,非是要出自武陵绣史之手。那一幅绣画,耗时多少年,藏于阁中,无人可有面缘,木主人专用一艘凤头龙尾琉璃瓦大船请走。从此,天南海北,路远迢迢,不得见其踪迹。就这,可也看出申府的家底已抖落得大致差不多了。然而,世事难料,这还不算完。等那棺椁一层桐油一层漆地上去,紫光和暗香一层桐油一层漆地透出来,无数遍,木本的光色气息依然居上风。终于完工,停在后重院专辟出的一间厅房,申明世绕棺走了几遭,十分欣悦安慰,对儿子柯海说:就此可以长眠不醒!不想,一语成谶,只是长眠不醒的不是申明世,而是申夫人。
早十几年,申明世就在二夫人房中起居,老夫人单住一个院,由仆佣侍候陪伴。这一日晚上睡下,早晨却没再起来,面色红润,神色安详,那具棺椁就由老夫人睡了。申明世说:择日不如撞日,夫人撞了这棺椁告成的日子,天意就是归她!上下都说老夫人有德,一生安分,不争不夺,又助老太爷亨达,所以才能善始善终。丧事办得隆重,将莲庵新漆一遍,添了两个小和尚,轮值长明灯。银子流水般花出去,不得已卖了几顷水田——这回是真卖了,不是虚传。做棺材办丧事,是两宗大开销,小花费就数不清了:大孙子阿昉开豆腐店亏蚀的钱;二孙子阿潜在外游荡赊欠的账;庶出的三孙子阿暆驯鹰养狗,一条大黄就是十数两金子。一个园子一处宅子,加砖添瓦,修树补草,清池子,砌甬道,此起彼伏,一刻不容迟缓,还是赶不上。好几处景都荒废了,宅子也明显旧了。老夫人出殡,将院墙刷了一遍,八扇大门油了新漆,别的还只能继续旧下去。
自大运河凿通,江南一带便是朝廷的钱粮地。元末时,张士诚割据苏松嘉湖,与太祖争霸,大明朝记着这笔账,洪武开元,就科以重税,无论天灾人祸,一粒谷子也不能少,延续至今。这些年,辽东女真部出了一个努尔哈赤,势力渐强,大有称王的气象,京师深感不安,暗中筹集兵力,加强戍边。于是税赋又加几倍,不时增出种种捐募。所以,不止申明世一家,也不止申明世这样挥撒,富户们个个都觉手紧,不得已节约用度。申家算来算去,暂时能缓解下来的,亦只有蕙兰出阁这一桩了。
之前,几个姑娘,即便是闵姨娘生的颉之颃之,奁资都很可观。田地、奴婢、金银器皿、绫罗绸缎,单是各式各样的铜锁,就有一抬箱。到了蕙兰,不由让人犯了难。但申家人生性都很乐天,心想三年的工夫,怎么凑不拢姑娘的一副嫁妆?再说,还有她外婆家呢。所以,一时难堪过后,又放下了,依着原样过日子。老夫人殁了,更没了管柬,比先前还任性许多。小绸与柯海不齐心,商量不了什么事,阿昉的女儿和她又隔一层;阿昉的媳妇呢,本来没什么心肺,倒也好,不愁不烦;却是希昭,有时候会替蕙兰着急。看一家人都没事人一样,以为三年时间过不完,闺女养不老,和阿潜说,阿潜道:我看她和你很好,要是出阁了,你不就没伴了?像是有意留蕙兰似的,就知道白说了。也和大伯母说过一回,大伯母低头想一时,抬头说:希昭一幅绣画,能换一副棺木,还换不来一套妆奁?于是,家中就传开二婶替侄女儿挣嫁资的话,传到蕙兰耳朵里,蕙兰就来找希昭,发难道:二婶你绣也白绣,我又不嫁!说罢便哭了。
这一年,蕙兰改了模样,原先圆鼓鼓的脸颊清瘦下去,成了长脸,圆眼也变长眼,眼梢细细地几乎入鬓,双睑便显得越发深了。口唇还保持着幼年时方正敦厚的形状,就这处地方,流露出天真娇憨的神情,不至于寒薄。此时,泪眼婆娑,像小孩子耍横,其实是有无限的委屈。希昭不忍说破,就也横着口气说:谁替你绣呢?申家何至于到这地步,要鬻女红了!蕙兰上前就夺希昭手里的针:我不让你绣!希昭躲着:我绣我自己的,管你让不让!蕙兰硬夺,希昭仍不松手,两人绕了花绷追逐了几圈,最后针是让蕙兰夺了,却刺破她的手指头,眼泪越发汹涌了。希昭握住侄女儿滴血的手指头,任由她哭一时,渐渐平静下来。希昭说:不过是你伯祖母一句玩笑,怎么就当真了!姑娘出阁,纵然是砸锅卖铁,也要好好陪送的!蕙兰戚楚一笑:咱们家怎么就到了砸锅卖铁的田地了!希昭发觉说错话,收回也来不及,只得极力补救道:当然不至于,松江地方,有的是咱们家的地,城里城外,又有店铺房子,又不是有几个闺女的,正出只你一个,要亏欠了,连外婆家也饶不过的!蕙兰不流眼泪了,眼圈还红着,默了一会说:外婆家也在卖地。希昭又发觉说错话,众人都知道,自彭老爷去世,几个舅舅便开始争产,等不及见分晓,就比着花钱,将那园子修葺了几遍,拆旧景,添新景,倒把沉香阁荒落了。沉香菩萨前的清灯,常常干了油没人去添。所以,那日新月异中,实已见得出潦倒。希昭也默了下来。
日光转移,希昭和蕙兰将花绷调了背向,希昭接着绣,蕙兰在一旁看。这时,阁中就这两个人,其余人做别的去了,格外安静。从窗户可看见池水,浮着几茎残荷,池边的花木也疏落了,已是入秋时分。蕙兰说:难道非要出阁吗?我就不嫁怎么的!希昭笑道:新路巷那边能放过你吗?蕙兰霎时红了脸,佯装又要夺希昭的针,希昭也佯装着告饶:不嫁不嫁!蕙兰恨声道:我自己给自己挣吃喝,谁也不能撵我!希昭知道蕙兰使气,并不回答,她就又接着说:就看看咱们家的那些爷们,身无长技,单知道花银子,说不定哪一天,真要靠咱们鬻针线养活他们呢!希昭抬头说:听说新路巷有个小廪生很是勤勉,日日挟着个青布书袋去县学点卯,挣廪膳呢!蕙兰又红了脸,都知道,年前张陛补了廪生。她要再去夺针,却只是虚抬一下手,说:不理你了!转身就走。希昭追了她的背影说:你妈要是不出阁就没有你呢!蕙兰听了这话站住了,回头菀尔一笑:二婶要不出阁,我也认不得二婶!希昭点头道:所以,出阁有出阁的好!蕙兰应道:那么就请二婶让一幅绣画,替我换嫁妆。希昭横她一眼:自己挣去吧!蕙兰腆着脸说:二婶何时替我备好嫁妆,我何时出阁!说罢,不容希昭回嘴,赶紧跑下阁去。
逗嘴玩笑,自可排遣郁闷愁烦,却也于事无补。时间如流水,一日一日过去,嫁妆的事依然不见眉目,家中人似乎都忘了,提也不提,事实上是一筹莫展。
做父母的,怎么会不将女儿的婚事上心,只是阿防素来与大伯母不亲,又是内敛的性子,就开不出口。小绸自然也要替蕙兰着想,终究是镇海媳妇的儿女子孙,但因与柯海负气,凡事都要他来请求商量。柯海不是没有心,只是有心无力,不晓得对小绸说什么,只好什么都不说。这些人各自在心里疼蕙兰,就是不通气。再则,申家的人在一处,从来是商量如何花银子,如何缺银子的事,彼此都觉得窘,就更难开口了。这么又拖了一年,眼看着到了第三年上,几乎是迫在眉睫,再也拖不下去了。最终,还是小绸起头,让阿潜带话给大伯,让卖几亩田地。小绸与柯海传话,向来不是商量,而是下令,因为晓得阿潜与大伯有些父子亲,自然会宛转款曲。阿潜带回来的话却令人沮丧得很,原来柯海早就在卖地,为的是家中几项人情往来:阿昉阿潜泰康桥的外公外婆,也就是采萍的公婆,先后过世,相隔不过三日,俗称“刀切豆腐两边倒”;希昭的祖父也在这一年作古;阿奎媳妇添子;采萍、颉之、颃之也添子添女。这些红白事在别家也许能轻易打发,但在申家,却非得兴师动众不可。一来是面子,二来也是习惯,不知该如何节制。徐光启中进士,其实与他们家干系并不大,可依照旧例,还是要在园子里摆宴席庆贺,自然就要再将园子整饬一遍,南北东西采办食材。凡事一旦出手,必轰轰烈烈。然而,这一回卖地却卖得不那么容易了,事实上,至今没有出手,不得已,在好几处赊着银子。所以,再要卖地,结果还是,赊账。小绸让阿潜再带过话去,赊账就赊账!柯海回过来的话带着商量的意思,那就直接用地作陪嫁?小绸就被噎住了。
成顷的地作陪嫁固然算得上慷慨,但嫁妆中的田地,往往是折成银子。尤其像张家这样的小户,靠生员的月米度日,纵然有几亩薄地,不过由人代耕,吃些零碎租子。猝然间,大块田地归于名下,凭空到哪里寻人管佃户,收租米,还要付税付捐,岂不是陪送了一个大累赘,让人觉得不诚心。就算田地作一份嫁妆,那还有别项妆奁呢。衣服、首饰、家什用具,哪一项能免?张家是贫寒些,可惟其如此更不能敷衍,申家又不是势利眼。总之,还是要卖地。
方才说了,富户们都手紧,顾不得买地。有新发起的,心思又多在商贾,海河路通,市肆兴隆,而田地多半是要靠天吃饭。这时候,小绸也出手了,自己的娘家,多年不通声息,如今走动起来;泰康桥那边,是两重亲家,自然更要往来;还有苏州胥口闵姨娘家,做了一世织工,大约也要置办些产业——因是亲戚,不能开门见山就谈卖田,总要嘘寒问暖,打点人情,预先又花销了交际费用。此时此刻,阖家上下一条心地卖地,倒把蕙兰的婚事搁放在一边,时间又过去小半年。这一日,小绸向希昭打听,她杭城里的娘家亲戚里头,有没有想买地的,希昭不由冷笑道:大娘真是病急乱投医,明知道沈家为市井百姓,哪里攀得上置地置产的主,这不是嘲笑我吗?小绸在这个侄媳妇跟前,本来就有些顾忌,不留意说错话,竟瑟缩起来,嗫嚅道:也不过是瞎问问,有当无的,不是火都上眉毛了吗?希昭自觉着言语太犀利,也不好意思,缓和下口气,说:要不再推迟一年半载?小绸叹气道:还有什么借口呢?丧期三年满了,人家小子二十一,我家姑娘十九,总不能还是年纪小,人家就算有耐心了。希昭说不出话来,婆媳俩默不作声坐着,希昭说:这幅《竹林七贤图》快收尾了,再加紧些,找个买主,拿去换银子!小绸不由也笑一声:难为希昭有这个心,可是怎么说呢?好比阮郎家的那堆方子,闲置多少年,正遇咱们家老爷奇思异想,要寻一段天外木头;又正巧阮郎别的都不稀罕,偏只器重武陵绣史的绣画,是彼此识货,又是投缘,还是知音,高山流水的——话说到此,希昭已经明白。这两人都是冰雪聪明,如若不是有层层隔阂,本应是最处得来。这一时,虽没说话,但心领神会。静了一会儿,希昭安慰道:大娘也不必太焦愁了,俗话不是说,船到桥头自然直?小绸说:可是,究竟直在哪个桥头呢?希昭噗嗤笑道:再遇一个知音,买了咱们天香园的绣画!小绸也笑了:希昭这样的鬼精,空手套得白狼,白饶了一副好嫁妆!希昭嘴也不让:大娘是瞧不上沈希昭的嫁妆,就说不要!小绸说:为什么不要?不要白不要!小绸正色道:无论遇不遇知音,总之,咱们卖地的卖地,绣画的绣画,老天不负有心人,就能把这船头直过来!希昭也正色道:照大娘的意思,蕙兰与张家那小子要是有缘,就能成事!两人说过这一番,彼此都松快些,分手各做各的去了。
张家这头,早在等着迎娶。三年中,每逢年节总要上门,送各色礼。统不过是些茶果糕饼,布匹针线,但都是张夫人亲来。平日里,张老爷也常有书信问候,心意十分诚笃。申家越发难以为情,不知如何应对才好。头丽年尚可说几句儿女婚事,日子越近越不敢提,最后索性不谈。张家人不免着急起来,不得已,回头再求冰人杨知县。杨知县一听情形,就已猜得个七八分。皇上一味敛银子,江南豪户全是大有大的难处,别人都在收缩,惟有申家张扬。杨知县早看出申家硬撑场面,近几年又出了那么些事,囊中必然空虚。其实,张家自己单薄,并不在意亲家的聘礼长短厚菲,但这话万不可对申家去说,说了等于是激将,申家人不仅爱面子,还人来疯。要知道有这一说,必当数倍数十倍地置办,反落了更大的难处。杨知县思忖几日,有了主意,立时备船备轿,动身往上海,专去见申明世。
自从申夫人过世,入殓了那具好棺木,申明世就再不提棺材的事。柯海每每提议再觅一方好木头,申明世便举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》里,“藏天下于天下”的意思,说,只需择一张好席子,卷一卷,深埋地下,就哪来的回哪去了!柯海以为父亲伤心,神情却不像,极安宁,甚至于含几分欣悦,且像是悟道,出世外,就也不敢多问。但见申明世身体日益健旺,精神矍铄,越过越年轻似的,棺材的事便不再提了。这天,杨知县忽然造访,原本备了一套悼丧的言辞,然而,不料想申明世神态怡然,就只淡淡说几句,再互问了近况,杨知县就道明来意了。
杨知县的来意是数年前他做的大媒,该择定吉日了。因是他牵的线,所以必要过问不可。那姑娘极小的时候见过,就十分喜欢,倘没有记错,外婆家是上海名宦彭家。申明世点头说正是,彭老爷过世,地方上集资,专造了“爱日亭”,铭记和缅怀。杨知县叹道,名门闺秀,金枝玉叶,原有一个想头,如今看来分明是妄念!申明世追问什么想头,如何又成妄念?杨知县笑着摇头道:本想向申老爷要来做干孙女儿,吃喜酒可坐上座,受新人们叩拜,现在一听说家世渊源,可不敢提了!申明世说:这有什么不敢的?那是丫头子的福分,明明是抬举了她!杨知县只是摆手说“不敢!”申明世非说“敢!”两人争执半时,最后,少的听长的,杨知县只得服从,遂又调侃道:富贵人家的小儿女,多有认穷干亲的,为了好养活,本人就是如此的干亲一个!申明世笑道:随怎样说,从此摆脱不了干系,那丫头就算赖上身了!说笑一番,又转回正事,杨知县道:这一来,真就要问一声,小女什么日子出阁?申明世一边遣人去唤柯海,一边叹道:这丫头的亲祖父母,一个早夭,一个出世,凡事都是由大伯祖、大伯奶作主,可恨这大伯祖大伯奶做了几十年的冤家,什么话都不好商量;自己的父母又都无能,父亲是个果子,母亲呢,大户人家的女儿,娇宠得很,难免不晓世事,是个长不大的孩子,不像她的婶婶——就是那个绣画的?杨知县问。你也听说了?申明世颇感意外。杨知县说:谁不知道“天香园绣”?谁又不知道“武陵绣史”,宋元书画皆成绣品,天下一绝!要说,还是同乡,钱塘杭城里的娘家。申明世谦词道:其实不过是些女儿家的针线,照理不该出闺阁的,露拙了不说,还坏规矩,偏巧新埠风气轻薄,就喜欢淫巧的玩物,一来二去倒收不回了!杨知县就不同意了:织造本就是天工开物一种,绣艺且精上加精,锦上添锦,天香园又是出神入化,老太爷千万莫贬低了,伤自家人志气事小,违拗天意罪过就大了!正说话,柯海就到了。
听说蕙兰的大媒上门,就知道是谈嫁娶,柯海不由心中叫苦。但终也知道躲是躲不过的,迟早都有这一日,所以,反倒安下心来,神情很笃定。拜见过后,杨知县直接就说下聘的事,明言道,张家不是殷富户,聘礼恐怕单薄,奁资就也不必过奢,免得张家不自在。果不出所料,柯海的英雄气概即刻上来:申家女儿陪嫁是有定例的,先不说张家,单是自己家里,也不可厚此薄彼!蕙兰总是依她姑姑采萍的尺度,否则,张家倒要以为我们鄙薄他们了。杨知县不禁笑起来:方才你父亲已认了我这门干亲,如此说来,申府发送孙女儿也是我发送,倘嫁资豪华,世人还以为杨知县做官敛了大宗的银子;再说,年景平淡,朝廷又加兵税兵赋,万不可招摇,无事生非。柯海这才勉强答应尽量俭朴些。杨知县又非得添一笔妆奁,说当年得老太爷惠赠桃枝,插扦在南门外义田,如今一片桃荫,何以回报?说罢,就在几上放下一张银票,数字虽不大,面子却大。接着就要柯海择日子,由他报给张家,日内就来下聘。
这么着,逼上梁山似的,蕙兰的婚事紧锣密鼓地开张。杨知县的银票,加上贱卖的几顷旱地,她母亲当年的陪嫁再补上些,小绸封了一盒古墨算作一份——私下嘱咐,此墨不单为写字,更可治产后血症,她祖母生叔叔阿潜时就凭了一角墨核渡过险关,得了几年阳寿。蕙兰先是羞红脸,然后又是煞白,小绸晓得将她吓着了,赶紧说并不是每每发生,不怕一万。只怕万一罢了!蕙兰这才缓过来。东西看起来也不少了,可七零八落的,显见得是拼凑起来,到底局促了。张家已来请尺寸单,要新娘裙袄的领口、身腰、款式,好着手做嫁衣,也是他家原籍的规矩。行聘之礼紧随着过来了:簪、环、玉如意、金手钏;这边勉强回过礼去:靴、帽、袍套、鞋袜,接着就要发奁了。事已至此,不成也成。
夜里,小绸兀自坐在房里,望着壁上的灯影。自己的洞房花烛夜还在眼前,灯火却已经阑珊。院里的香樟树长成巨大的一株,满庭的浓荫,屋子都遮暗了。心中怅惘,不知所以,忽然门帘一动,进来一个人,是蕙兰!小绸倒是一怔,将出阁的闺女,怎么还四处乱逛着,就笑道:这就睡不着了?蕙兰不回嘴,神情很正经。小绸收起笑,问:有事吗?蕙兰还是不说话,脸却渐渐红上来,眼睛里似乎汪着泪,亮晶晶的。小绸心下不安,强又笑道:有什么事快说,大伯奶好替你作主!蕙兰的眼泪到底屏住在眼眶里,吸一口气,终于说出来:我向大伯奶要一件东西!小绸一惊,惊的是这丫头真大胆,敢向她要东西,又不知她要的是什么,给得出给不出?嘴上说:尽管要,只要大伯奶有,准定给你!蕙兰说:大伯奶准定有,却不定舍得给我。小绸不觉有些恼,想这丫头人小鬼大,这么会纠缠,沉下脸说:你不说,我怎么知道舍得不舍得?蕙兰的眼泪全收回去了,脸上呈出一丝笑意,一歪头:说了啊?小绸被挑逗得气急败坏,伸手点在蕙兰额头上:我告诉你,要说赶紧说,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,舍得不舍得都不给了!蕙兰这才说出口来:我要天香园绣!小绸松下一口气:当你要什么宝贝!阁里去挑,要多少尽管拿。蕙兰摇头说:我要的是天香园绣的名号。小绸只觉得心里一沉,竟说不出话来。蕙兰再说:凡我申蕙兰绣下的活计,就可落款“天香园绣”。小绸回过神来,说:你出了这个阁,就不是申蕙兰,是张家的人了!蕙兰说:我不管,
“天香园绣”这四个字,就算是我的陪嫁!提到“陪嫁”两个字,小绸不作声了,谁让娘家对不起她呢?可是,小绸又想:这丫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憨傻,不知存着什么心!
30 张陛
张家所在新路巷,是三牌楼的背街上,顶着巷底的一处院落。似乎是从原先排好的台基上硬挤出来,正着挤不下,只得侧过来。新路巷的院子本是南北排列,东西向,这么一侧,倒侧成了坐南朝北。平时进出是从巷内的北门,南门临街,闭得多,敞得少,偶尔推开,远远可看见九间楼的后墙。在这一片闹市中,显得十分静穆。张家的院子多少是偏狭的,好在人口简素。倘从北门进去,先是一方天井,一眼水井,年头不小了,井壁上布了苔藓。天井两侧各是灶房和仆佣的屋子。走过天井,便是正厅,北墙上横一块匾,书几个大字:永思堂,匾下案上供一尊弥陀,一炉香,案两侧各置几具桌椅。厅堂东西厢房为老爷夫人居室与书斋。厅堂前是院子,院子两边各有连通的两间侧屋。东侧是哥哥张陞一家三口,西侧是弟弟张陛。
蕙兰自小在大宅子里,人多事多,申家又格外地有一番热闹,天天过年似的。来到张家,耳根子刷地静下来,每日所见不过有数的几个人。一日三餐节用得很,于是,家务便也是节用的。长年在家只两个仆佣,一个女人,做张夫人贴身活计,也照管老少爷们几个的起居,名字很奇怪,叫李大,仿佛是北地人的叫法。一个男厨子,兼顾采买、洒扫、种植花木,都叫他范小,可见出是年少时就来到家中,一路做下来的。张陛的媳妇年前生下孩子,又添了个奶母,这样,李大就免去张陞房里的杂役,多出的时间则放在张陛一处。张夫人特地叮嘱李大多照应新来的媳妇,过惯呼奴唤婢的日子,初来乍到,自然会有种种不方便。李大和范小都没有婚娶,大约这也是久留张家的缘故。
李大年纪在三十来岁,人长得很素净,宽平的额头,终年戴一条蓝布遮眉勒,除此,再无任何头饰。不裹脚,衣袖窄窄地系起,腰带扎紧了,做事走路都很利落。初与蕙兰见面时,双方都很拘谨,在李大是对名门闺秀的敬畏,蕙兰则因极少见自家以外的人。一旦说话,双方又都释然。李大看蕙兰不过是个小闺女,来到陌生地方,手足无措,颇有些可怜,即便是可怜却也不失大方,到底是大家子出来的。再说蕙兰看李大呢?神情虽呆板,倒并无瑟缩,看顾她的一瞥中,还流露出慈和。再相处几日,李大越发见出,这一个金枝玉叶其实不怎么挑剔,固然出于蕙兰自己的性情,但也还是因为大家子里的人事终究是复杂的,所以孩子们也多有约束检点,因而李大揪起的心便放了下来,态度也自如许多。蕙兰就发现,李大原来是个挺风趣的人。张陛去点卯,穿一袭玉色镶蓝的袍衫,袍衫有一股森严凛然,越发衬得那小廪生豆芽般的细嫩。李大就说是“苍蝇套豆壳”,蕙兰看了也觉得很像,笑个不停。于是,李大就知道,蕙兰是个活泼的小闺女。
范小则是个害羞的人,因没娶妻,就特别不能见女眷。蕙兰来了多日,都没见过他。只在天蒙蒙亮时,听到他的扫帚划过院里的青砖地,轻轻的“刷拉”一声,“刷拉”一声,也是很害羞的。李大知道他腼腆,却偏要寻他玩笑,院子里撞见时,就要说:让太太作主,咱俩一起过日子!只听得范小拖起扫帚就跑,李大还不放过,跺脚佯装追他。范小这年是十九岁。
仆佣们是这般有趣,主子呢,当
 权力玩家:历史上的大…
权力玩家:历史上的大… 解放战争系列主题题阅
解放战争系列主题题阅 当文艺女恋上理科男
当文艺女恋上理科男 现当代作家文集
现当代作家文集
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世界
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世界 毛泽东兵法
毛泽东兵法 犹太人为什么优秀
犹太人为什么优秀 《子不语》在线阅读
《子不语》在线阅读
 先锋警事备忘录(小说两…
先锋警事备忘录(小说两… 短篇小说:平行与垂直
短篇小说:平行与垂直 交警老龚的生死恋
交警老龚的生死恋 相约星期二
相约星期二
 卡尔威特的教育
卡尔威特的教育 家有小天才(家庭教育
家有小天才(家庭教育 千万小说在线阅读
千万小说在线阅读 美丽与哀愁——一个真…
美丽与哀愁——一个真…
 励志经典:做女人要像
励志经典:做女人要像 毕飞宇小说:推拿
毕飞宇小说:推拿 唐太宗-李世民传
唐太宗-李世民传 女
女
现当代作家
小故事大智
岑凯伦言情…
大功大过隋…
世界作家作
第二次世界
读者2011第
人生四大秘
寄秋言情小…
陈明娣言情…
《傅雷家书…
《青春的叛…
姚雪垠长篇…
霍桑探案小…
南湘野叟武…
《山海经》
席绢言情小…
朱维坚作品
天香 第三卷 设幔
29九间楼
万历二十八年,上海的大事情都与徐光启有关。一是徐家在原先的宅基破土动工,造新宅子。地处方浜以南,肇嘉浜以北,日涉园西,背依一条小河汉,名乔家浜,门开在正南,俞家弄内。新宅子总共三进,并排九间,上下两层,人称“九间楼”。宅子的样式没什么新奇,也无奢华,在富户云集,风气绮丽的上海,堪称质朴。但就是这质朴,却因占地广大,建制充实,而有一种阔朗,还有一种端肃。要说造房子,本不算什么大事情,但联系上另一桩,也就是第二件大事情,便未可小视了。也是这一年,徐光启在南京,又结识一个意国人,利玛窦。和仰凰一样,也是洋和尚,却是个大和尚,要去京师见皇上。皇上不喜欢洋教,可是喜欢洋玩意儿,利玛窦带了无数稀奇古怪的器物,晋见的路已经膛平。这时,正走到南京,和徐光启碰上了。这徐光启,正途颇不得意,二十一岁中秀才,之后连连落第,丁酉年,好不容易中乡试,而且第一名,隔年的会试却又失利!年华就在这屡试屡败中过去,和许多读书人一样,也许就在幕府中度过一生。然而,又有迹象,暗示事情并未到此结束。好比徐光启踯躅科场多年,不期然里一突进,谁能断定,再下一轮踯躅之后又会发生什么?在外交游,竟先后与两个意国人邂逅,千山万水的,又非我族类,其中藏有怎么样的机缘?如今,九间楼起来了,坐地居中,登楼远望,东边一条黄浦江,奔腾向海。那意国人,不就是从海上来,应了变通亨达。因此,两件事一贯穿,便成了大征候。
这是祥兆,凶兆也有,不算大,小小的一桩。就是城南有一农家,大牛生小牛,生一怪胎,两头六足。有一时人心惶然,谣言四起,转眼翻过年头,人春便是淫雨不止,淹了麦田,都以为应了那兆头,不会再有其他灾变。也果然平定下来,风调雨顺三载,就到了万历三十二年。也是方一入春,黄浦江上忽起两股龙卷风,黑水腾起数十丈,在空中交汇,纠缠格斗,沿江大树连根拔起,茅舍尽毁。人们正议论,这才真是应了三年前两首六足牛犊的象,不料,倏忽间天降喜讯,松江府两士子中试,一是上海徐光启,中进士,入翰林院;二是华亭乔一琦,中武举,任京营兵把总。于是,坊间又改口,再不提那两首六足犊,只说,江上二龙相会,实是大气候,出将入相,将相和。
九间楼向北,隔乔家浜,过艾家弄几条横街,三牌楼南端新路巷内,一座小宅院,亦有着一桩喜事,张家二公子娶亲。张陛这年二十一岁,媳妇十九,数年前就下了媒聘。按说是早二年就当迎娶,不防出了些事故。三年前,媳妇的祖母,也就是申家老夫人去世。张家北地人的籍贯上有规矩,嫁娶或不出丧事的当年,或就必是满三年之后。申家一报丧,张家就紧锣密鼓筹备起来,可申家却推辞了,说姑娘年幼,家中一向惯养,不太懂事,再调教两年出阁更好。这是面上的原由,内里则是银两紧促,一时办不出像样的嫁妆。
那年,申家老太爷四下里采树造寿材,一回三折,到底觅来好木头,做了一套棺椁。木纹理细腻如凝脂膏油,紫光浮动,又有一股暗香。无论木材商还是大木匠,都认不出是什么木。申明世不由想起当年造天香园的章师傅,兴许能说出个大概,掐指算来也是七八十的年纪了,都不知道在还是不在。如今,最明跟的人只能说出产地,必是北方干冷的寒带,那里凡物种都不容易存活,非是天择不能落地生根。因生长极慢,数十年,甚而上百年一轮,质地紧密,犹如铜铸。那香自然是树脂的气味,也是因紧实原故,初不散发,年深月久,芬芳才缓缓释出,如同雾起。如今有此异香,必在千年以上。坊间都传闻,申家为寻木已花费大笔的银子,等觅到木头,就再拿不出了。要用田地抵,木主人不要,指明要天香园绣,不是一般的天香园绣,非是要出自武陵绣史之手。那一幅绣画,耗时多少年,藏于阁中,无人可有面缘,木主人专用一艘凤头龙尾琉璃瓦大船请走。从此,天南海北,路远迢迢,不得见其踪迹。就这,可也看出申府的家底已抖落得大致差不多了。然而,世事难料,这还不算完。等那棺椁一层桐油一层漆地上去,紫光和暗香一层桐油一层漆地透出来,无数遍,木本的光色气息依然居上风。终于完工,停在后重院专辟出的一间厅房,申明世绕棺走了几遭,十分欣悦安慰,对儿子柯海说:就此可以长眠不醒!不想,一语成谶,只是长眠不醒的不是申明世,而是申夫人。
早十几年,申明世就在二夫人房中起居,老夫人单住一个院,由仆佣侍候陪伴。这一日晚上睡下,早晨却没再起来,面色红润,神色安详,那具棺椁就由老夫人睡了。申明世说:择日不如撞日,夫人撞了这棺椁告成的日子,天意就是归她!上下都说老夫人有德,一生安分,不争不夺,又助老太爷亨达,所以才能善始善终。丧事办得隆重,将莲庵新漆一遍,添了两个小和尚,轮值长明灯。银子流水般花出去,不得已卖了几顷水田——这回是真卖了,不是虚传。做棺材办丧事,是两宗大开销,小花费就数不清了:大孙子阿昉开豆腐店亏蚀的钱;二孙子阿潜在外游荡赊欠的账;庶出的三孙子阿暆驯鹰养狗,一条大黄就是十数两金子。一个园子一处宅子,加砖添瓦,修树补草,清池子,砌甬道,此起彼伏,一刻不容迟缓,还是赶不上。好几处景都荒废了,宅子也明显旧了。老夫人出殡,将院墙刷了一遍,八扇大门油了新漆,别的还只能继续旧下去。
自大运河凿通,江南一带便是朝廷的钱粮地。元末时,张士诚割据苏松嘉湖,与太祖争霸,大明朝记着这笔账,洪武开元,就科以重税,无论天灾人祸,一粒谷子也不能少,延续至今。这些年,辽东女真部出了一个努尔哈赤,势力渐强,大有称王的气象,京师深感不安,暗中筹集兵力,加强戍边。于是税赋又加几倍,不时增出种种捐募。所以,不止申明世一家,也不止申明世这样挥撒,富户们个个都觉手紧,不得已节约用度。申家算来算去,暂时能缓解下来的,亦只有蕙兰出阁这一桩了。
之前,几个姑娘,即便是闵姨娘生的颉之颃之,奁资都很可观。田地、奴婢、金银器皿、绫罗绸缎,单是各式各样的铜锁,就有一抬箱。到了蕙兰,不由让人犯了难。但申家人生性都很乐天,心想三年的工夫,怎么凑不拢姑娘的一副嫁妆?再说,还有她外婆家呢。所以,一时难堪过后,又放下了,依着原样过日子。老夫人殁了,更没了管柬,比先前还任性许多。小绸与柯海不齐心,商量不了什么事,阿昉的女儿和她又隔一层;阿昉的媳妇呢,本来没什么心肺,倒也好,不愁不烦;却是希昭,有时候会替蕙兰着急。看一家人都没事人一样,以为三年时间过不完,闺女养不老,和阿潜说,阿潜道:我看她和你很好,要是出阁了,你不就没伴了?像是有意留蕙兰似的,就知道白说了。也和大伯母说过一回,大伯母低头想一时,抬头说:希昭一幅绣画,能换一副棺木,还换不来一套妆奁?于是,家中就传开二婶替侄女儿挣嫁资的话,传到蕙兰耳朵里,蕙兰就来找希昭,发难道:二婶你绣也白绣,我又不嫁!说罢便哭了。
这一年,蕙兰改了模样,原先圆鼓鼓的脸颊清瘦下去,成了长脸,圆眼也变长眼,眼梢细细地几乎入鬓,双睑便显得越发深了。口唇还保持着幼年时方正敦厚的形状,就这处地方,流露出天真娇憨的神情,不至于寒薄。此时,泪眼婆娑,像小孩子耍横,其实是有无限的委屈。希昭不忍说破,就也横着口气说:谁替你绣呢?申家何至于到这地步,要鬻女红了!蕙兰上前就夺希昭手里的针:我不让你绣!希昭躲着:我绣我自己的,管你让不让!蕙兰硬夺,希昭仍不松手,两人绕了花绷追逐了几圈,最后针是让蕙兰夺了,却刺破她的手指头,眼泪越发汹涌了。希昭握住侄女儿滴血的手指头,任由她哭一时,渐渐平静下来。希昭说:不过是你伯祖母一句玩笑,怎么就当真了!姑娘出阁,纵然是砸锅卖铁,也要好好陪送的!蕙兰戚楚一笑:咱们家怎么就到了砸锅卖铁的田地了!希昭发觉说错话,收回也来不及,只得极力补救道:当然不至于,松江地方,有的是咱们家的地,城里城外,又有店铺房子,又不是有几个闺女的,正出只你一个,要亏欠了,连外婆家也饶不过的!蕙兰不流眼泪了,眼圈还红着,默了一会说:外婆家也在卖地。希昭又发觉说错话,众人都知道,自彭老爷去世,几个舅舅便开始争产,等不及见分晓,就比着花钱,将那园子修葺了几遍,拆旧景,添新景,倒把沉香阁荒落了。沉香菩萨前的清灯,常常干了油没人去添。所以,那日新月异中,实已见得出潦倒。希昭也默了下来。
日光转移,希昭和蕙兰将花绷调了背向,希昭接着绣,蕙兰在一旁看。这时,阁中就这两个人,其余人做别的去了,格外安静。从窗户可看见池水,浮着几茎残荷,池边的花木也疏落了,已是入秋时分。蕙兰说:难道非要出阁吗?我就不嫁怎么的!希昭笑道:新路巷那边能放过你吗?蕙兰霎时红了脸,佯装又要夺希昭的针,希昭也佯装着告饶:不嫁不嫁!蕙兰恨声道:我自己给自己挣吃喝,谁也不能撵我!希昭知道蕙兰使气,并不回答,她就又接着说:就看看咱们家的那些爷们,身无长技,单知道花银子,说不定哪一天,真要靠咱们鬻针线养活他们呢!希昭抬头说:听说新路巷有个小廪生很是勤勉,日日挟着个青布书袋去县学点卯,挣廪膳呢!蕙兰又红了脸,都知道,年前张陛补了廪生。她要再去夺针,却只是虚抬一下手,说:不理你了!转身就走。希昭追了她的背影说:你妈要是不出阁就没有你呢!蕙兰听了这话站住了,回头菀尔一笑:二婶要不出阁,我也认不得二婶!希昭点头道:所以,出阁有出阁的好!蕙兰应道:那么就请二婶让一幅绣画,替我换嫁妆。希昭横她一眼:自己挣去吧!蕙兰腆着脸说:二婶何时替我备好嫁妆,我何时出阁!说罢,不容希昭回嘴,赶紧跑下阁去。
逗嘴玩笑,自可排遣郁闷愁烦,却也于事无补。时间如流水,一日一日过去,嫁妆的事依然不见眉目,家中人似乎都忘了,提也不提,事实上是一筹莫展。
做父母的,怎么会不将女儿的婚事上心,只是阿防素来与大伯母不亲,又是内敛的性子,就开不出口。小绸自然也要替蕙兰着想,终究是镇海媳妇的儿女子孙,但因与柯海负气,凡事都要他来请求商量。柯海不是没有心,只是有心无力,不晓得对小绸说什么,只好什么都不说。这些人各自在心里疼蕙兰,就是不通气。再则,申家的人在一处,从来是商量如何花银子,如何缺银子的事,彼此都觉得窘,就更难开口了。这么又拖了一年,眼看着到了第三年上,几乎是迫在眉睫,再也拖不下去了。最终,还是小绸起头,让阿潜带话给大伯,让卖几亩田地。小绸与柯海传话,向来不是商量,而是下令,因为晓得阿潜与大伯有些父子亲,自然会宛转款曲。阿潜带回来的话却令人沮丧得很,原来柯海早就在卖地,为的是家中几项人情往来:阿昉阿潜泰康桥的外公外婆,也就是采萍的公婆,先后过世,相隔不过三日,俗称“刀切豆腐两边倒”;希昭的祖父也在这一年作古;阿奎媳妇添子;采萍、颉之、颃之也添子添女。这些红白事在别家也许能轻易打发,但在申家,却非得兴师动众不可。一来是面子,二来也是习惯,不知该如何节制。徐光启中进士,其实与他们家干系并不大,可依照旧例,还是要在园子里摆宴席庆贺,自然就要再将园子整饬一遍,南北东西采办食材。凡事一旦出手,必轰轰烈烈。然而,这一回卖地却卖得不那么容易了,事实上,至今没有出手,不得已,在好几处赊着银子。所以,再要卖地,结果还是,赊账。小绸让阿潜再带过话去,赊账就赊账!柯海回过来的话带着商量的意思,那就直接用地作陪嫁?小绸就被噎住了。
成顷的地作陪嫁固然算得上慷慨,但嫁妆中的田地,往往是折成银子。尤其像张家这样的小户,靠生员的月米度日,纵然有几亩薄地,不过由人代耕,吃些零碎租子。猝然间,大块田地归于名下,凭空到哪里寻人管佃户,收租米,还要付税付捐,岂不是陪送了一个大累赘,让人觉得不诚心。就算田地作一份嫁妆,那还有别项妆奁呢。衣服、首饰、家什用具,哪一项能免?张家是贫寒些,可惟其如此更不能敷衍,申家又不是势利眼。总之,还是要卖地。
方才说了,富户们都手紧,顾不得买地。有新发起的,心思又多在商贾,海河路通,市肆兴隆,而田地多半是要靠天吃饭。这时候,小绸也出手了,自己的娘家,多年不通声息,如今走动起来;泰康桥那边,是两重亲家,自然更要往来;还有苏州胥口闵姨娘家,做了一世织工,大约也要置办些产业——因是亲戚,不能开门见山就谈卖田,总要嘘寒问暖,打点人情,预先又花销了交际费用。此时此刻,阖家上下一条心地卖地,倒把蕙兰的婚事搁放在一边,时间又过去小半年。这一日,小绸向希昭打听,她杭城里的娘家亲戚里头,有没有想买地的,希昭不由冷笑道:大娘真是病急乱投医,明知道沈家为市井百姓,哪里攀得上置地置产的主,这不是嘲笑我吗?小绸在这个侄媳妇跟前,本来就有些顾忌,不留意说错话,竟瑟缩起来,嗫嚅道:也不过是瞎问问,有当无的,不是火都上眉毛了吗?希昭自觉着言语太犀利,也不好意思,缓和下口气,说:要不再推迟一年半载?小绸叹气道:还有什么借口呢?丧期三年满了,人家小子二十一,我家姑娘十九,总不能还是年纪小,人家就算有耐心了。希昭说不出话来,婆媳俩默不作声坐着,希昭说:这幅《竹林七贤图》快收尾了,再加紧些,找个买主,拿去换银子!小绸不由也笑一声:难为希昭有这个心,可是怎么说呢?好比阮郎家的那堆方子,闲置多少年,正遇咱们家老爷奇思异想,要寻一段天外木头;又正巧阮郎别的都不稀罕,偏只器重武陵绣史的绣画,是彼此识货,又是投缘,还是知音,高山流水的——话说到此,希昭已经明白。这两人都是冰雪聪明,如若不是有层层隔阂,本应是最处得来。这一时,虽没说话,但心领神会。静了一会儿,希昭安慰道:大娘也不必太焦愁了,俗话不是说,船到桥头自然直?小绸说:可是,究竟直在哪个桥头呢?希昭噗嗤笑道:再遇一个知音,买了咱们天香园的绣画!小绸也笑了:希昭这样的鬼精,空手套得白狼,白饶了一副好嫁妆!希昭嘴也不让:大娘是瞧不上沈希昭的嫁妆,就说不要!小绸说:为什么不要?不要白不要!小绸正色道:无论遇不遇知音,总之,咱们卖地的卖地,绣画的绣画,老天不负有心人,就能把这船头直过来!希昭也正色道:照大娘的意思,蕙兰与张家那小子要是有缘,就能成事!两人说过这一番,彼此都松快些,分手各做各的去了。
张家这头,早在等着迎娶。三年中,每逢年节总要上门,送各色礼。统不过是些茶果糕饼,布匹针线,但都是张夫人亲来。平日里,张老爷也常有书信问候,心意十分诚笃。申家越发难以为情,不知如何应对才好。头丽年尚可说几句儿女婚事,日子越近越不敢提,最后索性不谈。张家人不免着急起来,不得已,回头再求冰人杨知县。杨知县一听情形,就已猜得个七八分。皇上一味敛银子,江南豪户全是大有大的难处,别人都在收缩,惟有申家张扬。杨知县早看出申家硬撑场面,近几年又出了那么些事,囊中必然空虚。其实,张家自己单薄,并不在意亲家的聘礼长短厚菲,但这话万不可对申家去说,说了等于是激将,申家人不仅爱面子,还人来疯。要知道有这一说,必当数倍数十倍地置办,反落了更大的难处。杨知县思忖几日,有了主意,立时备船备轿,动身往上海,专去见申明世。
自从申夫人过世,入殓了那具好棺木,申明世就再不提棺材的事。柯海每每提议再觅一方好木头,申明世便举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》里,“藏天下于天下”的意思,说,只需择一张好席子,卷一卷,深埋地下,就哪来的回哪去了!柯海以为父亲伤心,神情却不像,极安宁,甚至于含几分欣悦,且像是悟道,出世外,就也不敢多问。但见申明世身体日益健旺,精神矍铄,越过越年轻似的,棺材的事便不再提了。这天,杨知县忽然造访,原本备了一套悼丧的言辞,然而,不料想申明世神态怡然,就只淡淡说几句,再互问了近况,杨知县就道明来意了。
杨知县的来意是数年前他做的大媒,该择定吉日了。因是他牵的线,所以必要过问不可。那姑娘极小的时候见过,就十分喜欢,倘没有记错,外婆家是上海名宦彭家。申明世点头说正是,彭老爷过世,地方上集资,专造了“爱日亭”,铭记和缅怀。杨知县叹道,名门闺秀,金枝玉叶,原有一个想头,如今看来分明是妄念!申明世追问什么想头,如何又成妄念?杨知县笑着摇头道:本想向申老爷要来做干孙女儿,吃喜酒可坐上座,受新人们叩拜,现在一听说家世渊源,可不敢提了!申明世说:这有什么不敢的?那是丫头子的福分,明明是抬举了她!杨知县只是摆手说“不敢!”申明世非说“敢!”两人争执半时,最后,少的听长的,杨知县只得服从,遂又调侃道:富贵人家的小儿女,多有认穷干亲的,为了好养活,本人就是如此的干亲一个!申明世笑道:随怎样说,从此摆脱不了干系,那丫头就算赖上身了!说笑一番,又转回正事,杨知县道:这一来,真就要问一声,小女什么日子出阁?申明世一边遣人去唤柯海,一边叹道:这丫头的亲祖父母,一个早夭,一个出世,凡事都是由大伯祖、大伯奶作主,可恨这大伯祖大伯奶做了几十年的冤家,什么话都不好商量;自己的父母又都无能,父亲是个果子,母亲呢,大户人家的女儿,娇宠得很,难免不晓世事,是个长不大的孩子,不像她的婶婶——就是那个绣画的?杨知县问。你也听说了?申明世颇感意外。杨知县说:谁不知道“天香园绣”?谁又不知道“武陵绣史”,宋元书画皆成绣品,天下一绝!要说,还是同乡,钱塘杭城里的娘家。申明世谦词道:其实不过是些女儿家的针线,照理不该出闺阁的,露拙了不说,还坏规矩,偏巧新埠风气轻薄,就喜欢淫巧的玩物,一来二去倒收不回了!杨知县就不同意了:织造本就是天工开物一种,绣艺且精上加精,锦上添锦,天香园又是出神入化,老太爷千万莫贬低了,伤自家人志气事小,违拗天意罪过就大了!正说话,柯海就到了。
听说蕙兰的大媒上门,就知道是谈嫁娶,柯海不由心中叫苦。但终也知道躲是躲不过的,迟早都有这一日,所以,反倒安下心来,神情很笃定。拜见过后,杨知县直接就说下聘的事,明言道,张家不是殷富户,聘礼恐怕单薄,奁资就也不必过奢,免得张家不自在。果不出所料,柯海的英雄气概即刻上来:申家女儿陪嫁是有定例的,先不说张家,单是自己家里,也不可厚此薄彼!蕙兰总是依她姑姑采萍的尺度,否则,张家倒要以为我们鄙薄他们了。杨知县不禁笑起来:方才你父亲已认了我这门干亲,如此说来,申府发送孙女儿也是我发送,倘嫁资豪华,世人还以为杨知县做官敛了大宗的银子;再说,年景平淡,朝廷又加兵税兵赋,万不可招摇,无事生非。柯海这才勉强答应尽量俭朴些。杨知县又非得添一笔妆奁,说当年得老太爷惠赠桃枝,插扦在南门外义田,如今一片桃荫,何以回报?说罢,就在几上放下一张银票,数字虽不大,面子却大。接着就要柯海择日子,由他报给张家,日内就来下聘。
这么着,逼上梁山似的,蕙兰的婚事紧锣密鼓地开张。杨知县的银票,加上贱卖的几顷旱地,她母亲当年的陪嫁再补上些,小绸封了一盒古墨算作一份——私下嘱咐,此墨不单为写字,更可治产后血症,她祖母生叔叔阿潜时就凭了一角墨核渡过险关,得了几年阳寿。蕙兰先是羞红脸,然后又是煞白,小绸晓得将她吓着了,赶紧说并不是每每发生,不怕一万。只怕万一罢了!蕙兰这才缓过来。东西看起来也不少了,可七零八落的,显见得是拼凑起来,到底局促了。张家已来请尺寸单,要新娘裙袄的领口、身腰、款式,好着手做嫁衣,也是他家原籍的规矩。行聘之礼紧随着过来了:簪、环、玉如意、金手钏;这边勉强回过礼去:靴、帽、袍套、鞋袜,接着就要发奁了。事已至此,不成也成。
夜里,小绸兀自坐在房里,望着壁上的灯影。自己的洞房花烛夜还在眼前,灯火却已经阑珊。院里的香樟树长成巨大的一株,满庭的浓荫,屋子都遮暗了。心中怅惘,不知所以,忽然门帘一动,进来一个人,是蕙兰!小绸倒是一怔,将出阁的闺女,怎么还四处乱逛着,就笑道:这就睡不着了?蕙兰不回嘴,神情很正经。小绸收起笑,问:有事吗?蕙兰还是不说话,脸却渐渐红上来,眼睛里似乎汪着泪,亮晶晶的。小绸心下不安,强又笑道:有什么事快说,大伯奶好替你作主!蕙兰的眼泪到底屏住在眼眶里,吸一口气,终于说出来:我向大伯奶要一件东西!小绸一惊,惊的是这丫头真大胆,敢向她要东西,又不知她要的是什么,给得出给不出?嘴上说:尽管要,只要大伯奶有,准定给你!蕙兰说:大伯奶准定有,却不定舍得给我。小绸不觉有些恼,想这丫头人小鬼大,这么会纠缠,沉下脸说:你不说,我怎么知道舍得不舍得?蕙兰的眼泪全收回去了,脸上呈出一丝笑意,一歪头:说了啊?小绸被挑逗得气急败坏,伸手点在蕙兰额头上:我告诉你,要说赶紧说,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,舍得不舍得都不给了!蕙兰这才说出口来:我要天香园绣!小绸松下一口气:当你要什么宝贝!阁里去挑,要多少尽管拿。蕙兰摇头说:我要的是天香园绣的名号。小绸只觉得心里一沉,竟说不出话来。蕙兰再说:凡我申蕙兰绣下的活计,就可落款“天香园绣”。小绸回过神来,说:你出了这个阁,就不是申蕙兰,是张家的人了!蕙兰说:我不管,
“天香园绣”这四个字,就算是我的陪嫁!提到“陪嫁”两个字,小绸不作声了,谁让娘家对不起她呢?可是,小绸又想:这丫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憨傻,不知存着什么心!
30 张陛
张家所在新路巷,是三牌楼的背街上,顶着巷底的一处院落。似乎是从原先排好的台基上硬挤出来,正着挤不下,只得侧过来。新路巷的院子本是南北排列,东西向,这么一侧,倒侧成了坐南朝北。平时进出是从巷内的北门,南门临街,闭得多,敞得少,偶尔推开,远远可看见九间楼的后墙。在这一片闹市中,显得十分静穆。张家的院子多少是偏狭的,好在人口简素。倘从北门进去,先是一方天井,一眼水井,年头不小了,井壁上布了苔藓。天井两侧各是灶房和仆佣的屋子。走过天井,便是正厅,北墙上横一块匾,书几个大字:永思堂,匾下案上供一尊弥陀,一炉香,案两侧各置几具桌椅。厅堂东西厢房为老爷夫人居室与书斋。厅堂前是院子,院子两边各有连通的两间侧屋。东侧是哥哥张陞一家三口,西侧是弟弟张陛。
蕙兰自小在大宅子里,人多事多,申家又格外地有一番热闹,天天过年似的。来到张家,耳根子刷地静下来,每日所见不过有数的几个人。一日三餐节用得很,于是,家务便也是节用的。长年在家只两个仆佣,一个女人,做张夫人贴身活计,也照管老少爷们几个的起居,名字很奇怪,叫李大,仿佛是北地人的叫法。一个男厨子,兼顾采买、洒扫、种植花木,都叫他范小,可见出是年少时就来到家中,一路做下来的。张陛的媳妇年前生下孩子,又添了个奶母,这样,李大就免去张陞房里的杂役,多出的时间则放在张陛一处。张夫人特地叮嘱李大多照应新来的媳妇,过惯呼奴唤婢的日子,初来乍到,自然会有种种不方便。李大和范小都没有婚娶,大约这也是久留张家的缘故。
李大年纪在三十来岁,人长得很素净,宽平的额头,终年戴一条蓝布遮眉勒,除此,再无任何头饰。不裹脚,衣袖窄窄地系起,腰带扎紧了,做事走路都很利落。初与蕙兰见面时,双方都很拘谨,在李大是对名门闺秀的敬畏,蕙兰则因极少见自家以外的人。一旦说话,双方又都释然。李大看蕙兰不过是个小闺女,来到陌生地方,手足无措,颇有些可怜,即便是可怜却也不失大方,到底是大家子出来的。再说蕙兰看李大呢?神情虽呆板,倒并无瑟缩,看顾她的一瞥中,还流露出慈和。再相处几日,李大越发见出,这一个金枝玉叶其实不怎么挑剔,固然出于蕙兰自己的性情,但也还是因为大家子里的人事终究是复杂的,所以孩子们也多有约束检点,因而李大揪起的心便放了下来,态度也自如许多。蕙兰就发现,李大原来是个挺风趣的人。张陛去点卯,穿一袭玉色镶蓝的袍衫,袍衫有一股森严凛然,越发衬得那小廪生豆芽般的细嫩。李大就说是“苍蝇套豆壳”,蕙兰看了也觉得很像,笑个不停。于是,李大就知道,蕙兰是个活泼的小闺女。
范小则是个害羞的人,因没娶妻,就特别不能见女眷。蕙兰来了多日,都没见过他。只在天蒙蒙亮时,听到他的扫帚划过院里的青砖地,轻轻的“刷拉”一声,“刷拉”一声,也是很害羞的。李大知道他腼腆,却偏要寻他玩笑,院子里撞见时,就要说:让太太作主,咱俩一起过日子!只听得范小拖起扫帚就跑,李大还不放过,跺脚佯装追他。范小这年是十九岁。
仆佣们是这般有趣,主子呢,当
古镜奇谭有没有第三卷
迷恋有第三卷吗?
流云仙旅 第三卷 第十八章
从哪里可以下载狼群第三卷
求迷恋junkie第三卷以后的
鉴鬼实录第三卷60张哪有
鉴鬼实录第三卷60章
植木的法则plus第三卷
急需北师大版九年级数学第三章测试卷
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第五单元测试卷那里可以下载
小学人教版语文第十二册第三单元测试卷
植木的法则plus第三卷出来了吗?
植木的法则第三卷出来了没有啊?
cs小说中国战队第三卷那里有啊
谁知到《现代复仇记》第三卷在那
请问哪里有[魔法kiss]第三卷啊??
完美小姐进化论第三册从第几卷开始
六年级的综合测试卷中,综合卷五中的“四盘礼品”短文,第三个问题
怎样把第三方浏览器设为首选浏览器
谁有七年级科学上水平测试卷第三章(1-3节)的试卷?
请问各位哪里有《COCOON魔茧少女》第三卷下载啊?
那里可以找到牛津英语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练习卷
植木的法则plus第三卷出了吗?什么时候出啊?
急求电子书Donald Knuth 《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》的第三卷以后的部分?